大陸中心/唐家興報導
 宋代城市經濟蓬勃、文化開放,除了傳統的女妓外,男娼成為新興職業。(影視示意圖/翻攝自百度百科)
宋代城市經濟蓬勃、文化開放,除了傳統的女妓外,男娼成為新興職業。(影視示意圖/翻攝自百度百科)在宋朝社會裡,即便官方高喊「存天理、滅人欲」,男娼、牛郎店卻在繁華的都城悄悄盛行,形成一股奇特又難以遮掩的風月現象。特別是深鎖宮中的宮女,長年被悶在高牆內,一旦獲得短暫自由,竟成為牛郎店的固定客層,這段隱秘歷史,也成為宋朝性文化中最具戲劇性的篇章。
「宋代牛郎店的真相」:男娼風氣從宮門外一路燒到民間
宋代城市經濟蓬勃、文化開放,夜生活也隨之多彩起來。除了傳統的女妓外,男娼成為新興職業,男子化名、著女裝、塗脂抹粉,在京城的紅燈區成群出現,一時間成為獨特的都市景象。
據《清異錄》記載,當時北宋汴京的男娼數量「將乃萬計」,甚至有特定場所被稱為「蜂窠」(窠注音 ㄎㄜ,鳥、獸、蟲類等棲息的巢穴):意指密集聚集的男娼店,誇張到如蜂巢般蓬勃。
「蜂窠」裡的牛郎:偽娘般的妝扮、專業化的服務
宋代的牛郎多以女性化的名字登場,穿著女裝、蓄長袖、貼粉抹脂,談吐也刻意模仿女子。他們不只接待男客,更會為女客提供陪伴乃至性服務,功能完全不同於更早期只供豪門男士玩賞的「孌童」角色。(孌童,注音ㄌㄨㄢˊ ㄊㄨㄥˊ,舊時供人狎玩的美男子。)
當時的記錄顯示,他們甚至有頭目制度,如《癸辛雜識》中提及的「師」「行頭」,等同今日店內管理階層。
 宋代的牛郎多以女性化的名字登場,穿著女裝,談吐也刻意模仿女子。(影視示意圖/翻攝自百度百科)
宋代的牛郎多以女性化的名字登場,穿著女裝,談吐也刻意模仿女子。(影視示意圖/翻攝自百度百科)「主顧是誰?」深宮宮女與貴婦,成了最神祕的常客
宋朝牛郎店最令人意外的客層,不是士大夫,也不是市井女子,而是:「深鎖深宮、終日寂寞的宮女」、「孤寡貴族女子、官宦家婦女」。
宮女長期不得出宮,一旦有機會暫行外出,便瘋狂逃向蜂窠。《宋史》甚至記錄:某年正月望日,宋理宗與皇后微服出巡,一批宮女趁隙外出後「皆淫奔而不返」,整批人跑去牛郎店尋歡,震驚朝廷。
貴婦方面,《宋書‧五行志》更描述她們「三三兩兩結伴而行」,外出尋找牛郎排解寂寞,造成夫妻失和、家庭不睦,不少社會案件由此而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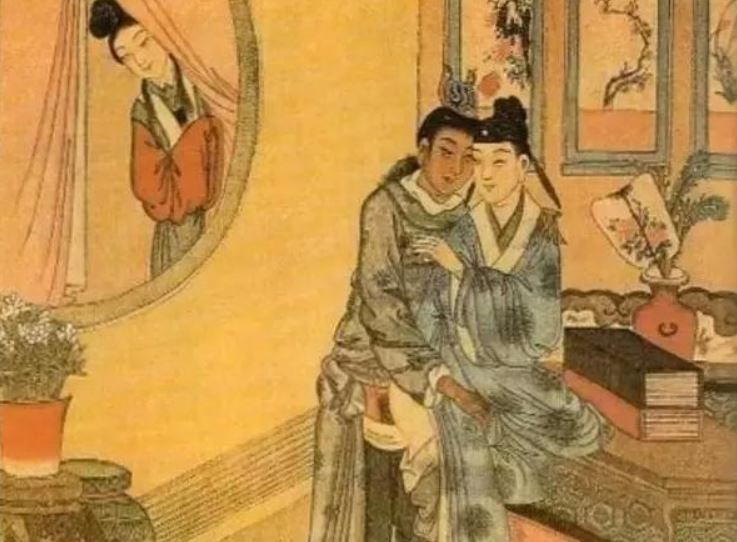 學者揭:宮女、貴族女性成為當時牛郎店最大客群。(圖/翻攝自百度百科)
學者揭:宮女、貴族女性成為當時牛郎店最大客群。(圖/翻攝自百度百科)「官府震怒」:抓、罰、恐嚇,卻越禁越盛
面對蜂窠蔓延,朝廷曾嘗試強制取締。政和年間,官府頒布「禁男淫文」,規定:「男為娼,杖一百;檢舉者賞五十貫。」
甚至還出現駭人的言論,主張要「斷其鑽刺之根,塞其迎送之路」,以暴力威脅男性娼妓「永久退出市場」。但效果極差,南宋時期因金兵不再頻繁南侵、社會相對繁榮,風月文化反而更加熾盛。
「為何在宋朝爆發?」理學高壓道德,反讓人性更反撲
諷刺的是,男娼盛行的背後,與宋代追捧的理學思想脫不了關係。程朱理學強調「存天理、滅人欲」,將人性慾望視為不潔,形成無形壓力。長期壓抑之下,群體性的反動便在地下空間爆發,使男娼、牛郎店形成更奇特、更蓬勃的文化景象。
明代學者謝肇淛在《五雜俎》中也批評:「男色之興…由宋人道學。」意指正是理學的嚴苛,使民間性文化更極端、更隱晦地蔓延。
結語:宋朝牛郎店,是繁華與壓抑共同催生的奇景
宋朝的牛郎風潮既是城市繁榮的副產品,也是高壓道德的反作用力。從蜂窠密布,到宮女成群「出逃尋樂」,再到官府嚴禁不成,男娼文化成為宋代最具戲劇張力的一段社會真相。而最終也回答了那個核心問題:宋朝牛郎店的主顧是誰?不是市井女人,而是深宮宮女、孤寡貴婦與高門女子。
 5 顆
5 顆  10 顆
10 顆  15 顆
15 顆  20 顆
20 顆